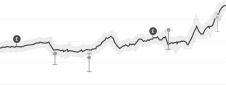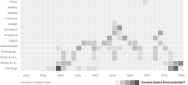Hanging scroll; ink and colour on paper
说 明 内收《老少年曲》、《菩萨蛮·忆杨翠喜》、《为老妓高翠娥作》、《赠歌郎金娃娃》、《将之日本留别海上同人》等李叔同诗词十一首。
展 览
1.“当时明月在-丰子恺文翰家珍”,香港会议展览中心,2018年9月28日至10月4日。
2.“漫画人间—丰子恺的艺术世界”,中国美术馆,2018年10月25日至11月3日。
来 源 此件作品征集自画家家属。
千金难买韶华好 风风雨雨忆前尘
—丰子恺《李叔同先生诗词》赏析
丰子恺十七岁时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遇见恩师李叔同,即后来的弘一法师。“那时我是预科生,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。”弘一的人生境界影响了他的一生。1918年,弘一将入山修梵行,丰子恺与刘质平作为他的护法随侍左右;弘一法师为丰子恺取宅名为“缘缘堂”、法名“婴行”;再至广为传诵的《护生画集》,二人师徒情深的约定持续了大半个世纪。
丰子恺回忆恩师总结道:“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,又变而为教师,而为道人,四变而为和尚。每做一种人,都十分像样。我崇仰弘一大师,是因为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。”
李叔同出身于津门巨贾之家,是一个早慧的天才,十岁时已经熟读诗书,旧体诗词写的极好,又先后师从名家学习篆刻、书法和戏曲,年纪轻轻已名列艺林。年轻时,他是“翩翩浊世佳公子”,曾“走马章台,浪迹燕市,厮磨金粉”,轻歌曼舞,陶醉于声色之娱,与坤伶杨翠喜、歌郎金娃娃、名妓谢秋云、诗妓李苹香等的密切来往为人津津乐道。
上世纪初叶,少年李叔同耽乐于“粉墨登场地”,是孙菊仙、杨小楼、刘永奎等名角的铁杆票友。彼时李叔同常常出入天津名园“天仙园”,园中红伶杨翠喜,样貌伶俐、嗓音出众,擅长梆子戏,辅一登场便引来满堂喝彩。李叔同经常去为她捧场,散场后还提着灯笼陪她回家。一来二去,暗生情愫。正是十七八岁情窦初开,李叔同为追求杨翠喜情根深种。然彼时杨氏追求者甚重,后又卷入一件震动朝野的“献美贿官”花案。使李叔同心灰意冷,陷入“少年维特的烦恼”。1905年春,李叔同作《菩萨蛮·忆杨翠喜》“花如雪”、“人如月”、“ 情长忘却游丝短”,极写杨翠喜之娇美婉丽,以及自己的相思之情。
这一时期他感情丰沛,英雄美人的倜傥情怀令他作出许多情诗,《金缕曲·赠歌郎金娃娃》“走马胭脂队里”、“片玉昆山神朗朗”、“英雄气宇, 秋娘情味”;《诗赠艺妓谢秋云》“故国天寒梦不春”、“为谁愁怅为谁颦”。尽是年少气盛、慷慨激昂。这时期他常常也亲自登台,饰演的黄天霸、十一郎、褚彪等形象都是绿林英雄, 与他“领略那英雄气宇”的初衷十分相符。
1905年秋,李叔同登上东渡的轮船赴日本留学,将满腔的豪情壮志投射到家国大爱中去,充满革新精神。《将之日本留别海上同人》即创作于此时。从“说相思、刻骨双红豆”到“是祖国,忍孤负?”“破碎河山谁收拾?”“听匣底、苍龙怒吼。”“二十文章惊海内,毕竟空谈何有?”,欲将“空谈”转而为“实干”。他与同学创办了春柳社,提倡话剧,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话剧团体。1907年,“春柳社”在东京上演了《黑奴吁天录》,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部话剧。之后,他在舞台上大放异彩,“茶花女”一角的成功,被评为是“在中国放了新剧的烽火”。
李叔同的人生一直在热烈燃烧、努力升华,由戏剧而艺术而宗教。他的高足丰子恺将之概括为:“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:一是物质生活,二是精神生活,三是灵魂生活。……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,就住在第一层,在世间占大多数;其次,高兴走楼梯的,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,这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,在世间也有很多;还有一种人脚力大,再爬上三层楼去,这就是宗教徒了。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,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,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、宇宙的根本,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。而我们的弘一大师,是一层一层地走上去的……”
对于丰子恺来说,恩师对他的启发是点点滴滴、方方面面的,教育他同样擅长诗词音律、具有多方位的修养和才华,感召他人情炼达,成为他漫漫人生路上的指路明灯。1929年,为庆祝弘一法师五十寿辰,绘画护生画共五十幅,由弘一法师作对开题识,集成《护生画集》。后由开明书店印行。至1939年,《护生画集》(第二集)六十幅完成,丰子恺承诺弘一大师持续作护生画直至其百岁寿辰。他的心志与恩师颇为契合,这份默契贯穿始终。恩师的“诗词”一直熟读在心,时时记起,念念不忘。
晚年提笔再忆《李叔同先生诗词》,时光荏苒、沧海桑田,却正是“诗词”中早己洞悉的世界:“浊世半生人渐老”、“梦里家山渺何许”、“有千金,难买韶华好”、“风风雨雨忆前尘”、“红楼暮雨梦南朝”、“都在书生倦眼中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