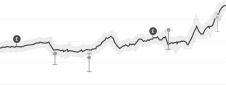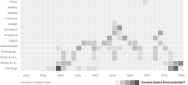Signed Binhong, with two artist seals
上 款 “宗陈”即冯宗陈,为黄宾虹先生入室弟子,擅绘事篆刻。随黄宾虹学习绘画、书法和篆刻,深得黄宾虹真传。
竞买本件拍卖标的,需办理高估价竞买号牌。
冯宗陈旧藏编号:347 - 348
夕阳山外山
—冯宗陈旧藏宾翁山水、花卉奇品
黄宾虹八十九岁作品素来难求,也向为市场所重。此时的宾老随心所欲,天人合一,眼底波澜,笔底烟霞。此季幸得冯宗陈先生收藏宾老八十九岁山水、花卉各一帧,极为少见,堪称奇品。
八十九岁的黄宾虹仿佛一位老拳师,如入无人之境,无招胜有招,且屡有“奇招”,故宾老八十九岁屡有“奇品”现世,有若羚羊挂角,无迹可寻。此时宾老站在西泠桥畔,回望栖霞岭的晚霞,夕阳山外山。
五代山水画家荆浩说,作画要“搜妙创真”。“妙”是客观的存在,也是画家的感受,“搜”是需要画家的主观努力。“搜”得“妙”与画得好的关系最密切,也就要求了画家必须要有生活,必须勤搜妙。黄宾虹在这方面有其胜人之处。他曾说“纵游山水间,既要有天马腾空之动,也要有老僧补衲之沉静”。这两句话,前者是他对山水的热情,后者是他对山水的细心观察和冷静思考,因此然对山川的理解比较深。也正是能“搜”得“妙”,所以他的画立意奇、丘壑多。到了高龄,在实在不能登山越岭时,只要稍加思索,就得到“昔年游览地,都上画图来”。
遵循古人之所教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黄宾虹行遍中华名山大川,尤其是晚年的巴蜀之游,发生于黄宾虹古稀变法之时,对其艺术风格的变化可谓影响深远。1932年秋,69岁的黄宾虹应友人之请入蜀游览写生,他溯江而上,经武汉、重庆,沿江又到叙州,入岷江,而上峨眉山,翌年春,在成都代陶冷月在四川大学教课数月,并漫游青城。后由成都出发到龙泉驿,过简阳,经乐至、射洪、蓬溪、南充、渠县等地至广安,游天池。再沿嘉陵江回重庆,由重庆乘轮船东还,览长江三峡之险,整个游程历时近一年,得画稿千余幅,诗文七十余首。巴蜀壮游,是黄宾虹历时最久、行程最远、收获最大的一次,也成为他艺术风格转变的关键。
其中尤其是蜀中名山峨眉山,黄宾虹更是于山中名胜处处留心写生,如金顶、乌尤寺、九顶山、伏虎寺、洗象池等。这些积累在日后创作时给了他无穷的灵感。
本幅《峨眉山洗象池》即黄宾虹于1952年89高龄时的精品之作,此时距他深游峨眉已经过去了20年,但洗象池的景致依然清晰。“洗象池”传说为普贤菩萨骑象登峨眉山时,汲水洗象之地,尤以皓月晴空之际、“象池夜月”之景着称。画中峨眉山麓几乎占满画面,浓墨、设色,层层积染至黝黑,但润泽如玉、浑然如雕塑般,具有撼人心魄的体量感,画境单纯而丰富,密实中隐约的虚白处最具妙理,天然而通透,山体内在的呼吸与天外云气共吞吐。
在画中,黄宾虹先勾勒点染,画出大轮廓,然后稍加皴,再以各种不同浓淡和干湿的墨色和彩色去点染。画中的点不止他常用的平点、竖点、大浑点、侧笔点、胡椒点等,还有一种代替线作用的点,即以点代皴,也用以分阴阳层次。在用墨点染之外,黄宾虹更以赭石、朱砂等颜色点染,黄宾虹认为画中“墨气未足,偶以淡色补之”。他基本不用调色盘上的颜色,而是把画纸当作设色对象和“调色盘”,依色彩的不同去点染不同地方,如画中的山,几乎看不出树,但经过点彩,立即给人以“依稀万木荣”的感觉。而远山则以石绿混墨,任其化开,一片融洽,别有风味。最后再以黄宾虹独创的水法,铺水一遍,使得画面浑厚华滋,意度俱足,山水间多出空灵之感,画尽而意无穷,更达到其想表现“峨眉山洗象池雨后”之景。
黄宾虹80岁时,他患上了白内障的眼疾,因此视觉渐渐消失,当他89岁那年,他的视力已经差不多完全消失了。可这对他作画丝毫不影响,虽然眼睛几近失明,但他那以书法为基础的用笔技巧已有八十年的经验,故而她的画可以说是不用眼睛看也可以顺手成画。此时的黄宾虹创作欲望最为激昂,更敢于放胆尝试笔、墨、色、水等各种绘画语言表现的可能和极限。
而且饱受着眼疾的困扰,此时如绘就一些小尺幅的作品或许会相对较为容易,但黄宾虹却偏偏选择了7平尺之幅的创作,这既是表明了黄老晚年笔墨技艺炉火纯青以及超强的自信,更是赋予了这幅《峨眉山洗象池》非同寻常的意义。画中上款“宗陈先生”即冯宗陈先生,他与许葆安皆是黄宾虹的入室弟子,随黄宾虹学习绘画、书法和篆刻,深得黄宾虹真传,二人每日请益,黄宾虹更是倾囊相授。得意门生求画,必定选择得意之作相赠方能称意。
黄宾虹虽然以山水画名世,但是他在花卉艺术上别有造诣。山水是拿手好戏,花卉则是他陶情适性之作。虽得自古人之法,但笔法、设色,乃至布局皆不同于古人,完全另辟了一个世界,看起来淡静古雅,使人胸襟舒适,却又无须要宋人那样“认桃无绿叶,辨杏有青枝”来刻画出花卉来,一见就知道是他画的那一种花。
一如本幅《东篱秋色》,采用低视点近景取图,将描绘的重心放在盘曲向上的整株花草之上。在此,黄宾虹以中锋用笔,逆势而上,表现茎叶。笔到之处,如石工凿字,不巧媚、不浮华。又以顺笔勾花,轻快自如,青绿罩染茎叶、赭石赋就花瓣、淡黄点染花苞,花中更有一只螳螂回首相看,更显生机盎然。鲜活、茁健、挺拔、韧性,小花草里有大气度,这是作品给观众留下的深刻印象。
中国古代画论中,向有“遗貌取神”之说,黄宾虹对花鸟之美要在遗貌取神、似而不似、不似之似的体会结晶。具体到这件作品而言,所谓“似”,是画中花卉实有其现实渊源和根据,所谓“不似”乃是黄宾虹以金石、篆籀之用笔,提炼和塑造花卉草虫,即以艺术手段(笔)透过表象(貌)去表达本质(神),宋人陈去非有诗道:“意足不求颜色似,前身相马九方皋。”黄宾虹的花卉,就在于“意足”,看去笔墨无多,却是生意盎然。因此艺术手段的高低就至关重要,对此,黄宾虹自己曾总结说:“笔能留得住,由点之连续而成,则有盘曲蜿蜓之姿,即篆隶法也,观唐宋人画,有深厚处皆如是。盖笔愈厚则神愈清,使笔要提得起,则缓处不妨缓,快处可更快,自能变化灵活,刚健中含有婀娜之致,劲利中而带和厚之气,洵称入妙。”
潘天寿激赏黄宾虹的花鸟画,认为“宾翁间作花鸟草虫,布置稳实而有法,设色清雅而华滋,杂似周之冕、恽寿平者,故无时下风习耳。”他曾说:“人们只知道黄宾虹的山水绝妙,花鸟更妙,妙在自自在在。”潘天寿本意毋宁在于其花鸟妙于山水,不如说正因其山水画之绝妙,才尤彰显花鸟之自由高妙。
“他基本不用调色盘上的颜色,而是把画纸当作设色对象和“调色盘”,依色彩的不同去点染不同地方,如画中的山,几乎看不出树,但经过点彩,立即给人以“依稀万木荣”的感觉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