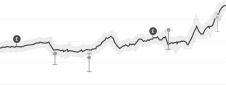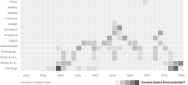張大千 印度少女獻花舞
設色紙本 鏡框 一九五一年作
款識:悅詩仁弟將返上海,寫此以贈其行,歸示稚柳、祖韓、秋君諸友,何如三年前畫也。情隨境遷,運筆遂異。辛卯七月初五日,張爰。
鈐印:「張爰」、「大千」、「昵燕樓書畫印」、「老棄敦煌」。
上款:「悅詩」即錢悅詩(1919-2013),江蘇常州人,大儒錢名山幺女,幼秉庭訓,諳詩詞、書畫,為龐左玉高足。錢家纍世書香,與同里謝氏交善。錢名山姑母,乃謝玉岑、稚柳祖母,謝氏昆仲先後入讀寄園。玉岑後娶錢氏長女,鶼鰈情深,惜夫人不幸早逝,大千以其閨名「素蕖」,為寫白蓮百幅,錢悅詩觀之大爲折服,遂興入大風堂之願,卻苦無機會。直至一九五一年春,她赴香港探望二姐,恰逢大千自印度來,經由二姐夫、著名報人、時任國民黨中央委員之程滄波引介,拜入大風堂門下。其既出名門世家,又是大千情逾手足之亡友謝玉岑妻妹,格外得其青眼,在港時,頻至老師處聆教。是年七月,錢悅詩行將離港歸滬,大千特寫本幅壯行,更與師母親至車站送別,垂愛若是,可見一斑。
註:一九五〇年初,張大千於印度舉辦展覽,展畢即四出考察遊覽,流連忘返,五月上旬,賃居於印北風景勝地大吉嶺,直至次年八月方舉家搬離。這一時期是大千創作的巔峰階段,彼時目力、精力最旺盛,作品無不細心經營,特別是工筆山水、人物最見精彩,且因與當地人接觸,頗有描繪印度風物人情之作品。
本幅寫於一九五一年「七月初五日」,陽曆在八月七日,彼時大千甫結束大吉嶺寄居,暫棲於香港,但作品中仍流露印地痕跡。少女雙手持一支紅蓮,輕盈起舞,作獻花狀,裙裾衣袂隨之飄揚。其額前、眼角、櫻唇點畫朱紅,戴額飾、耳墜,髮髻簪紅花,配項圈、手環、臂釧,身裹薑黃紗麗,乃典型印式妝扮。體態健美,腰肢玲瓏有致,不似一般中國仕女之纖柔含蓄,頗具異域情調。惟少女開臉乃出諸三白法,輔以赭紅襯托,明眉秀眸,使臉龐更偏「中國化」,流露婉約氣質。
從存世畫跡所見,大千取舞蹈入畫者極罕,但早於一九四五年,尚未赴印時,他見好友葉淺予所寫〈印度獻花舞〉,便「愛慕無似」,並以之為藍本摹寫,惟其舞者乃手托花籃,本幅改為手持蓮花,或為畫家目遇當地舞蹈所得。舞娘以工細之筆出之,綫條匀細而勁挺,乾净利落,收放自如,勾摹出少女妖嬈體態,亦帶出舞動之韻律感。荷梗之修長、衣擺之婉轉,尤見畫家運筆功力。色彩明麗,以赭黃、白粉為基調,蓮花、妝髮、配飾、衣帶處塗朱紅,愈加醒目,彰顯印地女郎艷麗嫵媚之風姿,正所謂「情隨境遷,運筆遂異」,無怪乎大千信心滿滿,冀以此向謝稚柳、李秋君等滬上諸友展示別後之藝術進境。
舞娘之手足心,皆敷赭紅,乃「緣如來八十種隨好,手足赤銅色也」。五〇年,大千於印北泰戈爾故地「寂鄉」欣賞當地舞蹈後所寫之〈寂鄉舞〉及這一時期的印度佛像作品中,均具此特徵,大千謂敦煌壁畫中,亦見有此相者。另,舞者手部關節之刻劃,不渲染背景以突出主體人物之處理,俱可見敦煌藝術之影響。
錢詩悅撰文道,張大千寫本幅時,她陪侍在旁,老師邊畫邊講解畫理,畫畢,懸掛於畫室,恰有客來,觀之笑稱一望即知乃為她所寫,因大千畫仕女,往往送誰便畫得像誰,對照錢悅詩容貌,確實頗有神似處。四五、五〇兩本印度舞,舞娘皆扭轉身姿,臉龐半掩,意在凸顯曼妙身姿,而本幅則以正臉示人,或贈佳人故也。
一九八三年,上海博物館、中國美術館相繼舉辦〈張大千遺作展〉,其中一九五一年所寫之〈執蓮仕女圖〉,由錢悅詩借展,創作年份、題材均與本幅吻合,當年展覽者,似即本幅。
參考資料:張大千一九四五年作〈印度獻花舞〉可參見〈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〉目錄,高美慶編(香港,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,一九九三年),圖版12
一九五〇年之〈寂鄉舞〉可參見〈香港蘇富比二十週年(1973-1993)〉(香港蘇富比有限公司,兩木出版社,一九九三年),圖版689
錢悅詩紀念老師文章〈雪門瑣憶〉可參見〈張大千生平和藝術〉(北京,中國文史出版社,一九九九年一月),頁244-246
105 x 52 cm 41⅜ x 20½ in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Zhang Daqian (Chang Dai-chien, 1899-1983)
1899 - 1983
Dancing Indian Girl
ink and colour on paper, framed
signed, dated 1951, with 4 seals of the artist
105 x 52 cm 41⅜ x 20½ in.